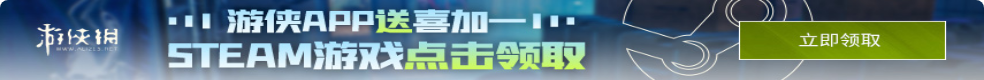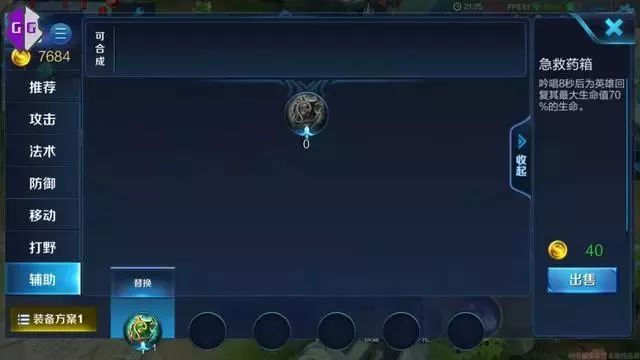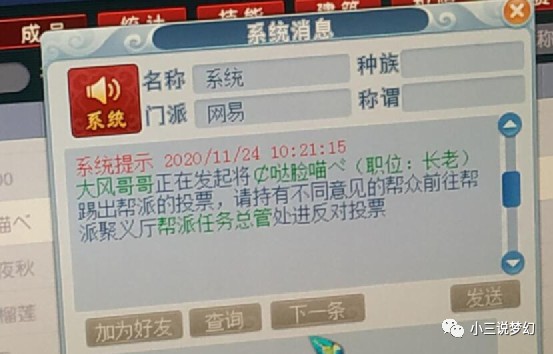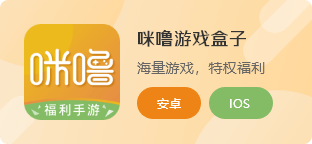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,总台加沙报道员阿纳斯·纳贾尔的朋友圈里,全是凌晨三点的废墟——他裹着磨得起球的防冲击背心,举着缠满胶带的话筒,把镜头对准炸塌的学校、哭着找妈孩子,还有蹲在路边啃干面包的老人。"我得让世界听见加沙的呼吸,"他之前跟同事说,"哪怕每句话都沾着灰。"
但10月下旬的一次报道,让他的"呼吸"停了半拍。那天他跟着救援队伍赶到耶路撒冷大街附近的空袭现场,刚要问旁边的志愿者"这里是哪个街区",突然看见瓦砾堆里露出半只粉色的小鞋子——那是他上周刚给7岁女儿买的,女儿说"像加沙春天的桃花"。他的手开始抖,话筒差点掉在地上,直到救援队员喊"这里有活人",他才踉跄着扑过去,扒开碎砖时摸到了妻子的衣角——她抱着女儿缩在卫生间的墙角,额头上渗着血,看见他的第一句话是:"你终于回来了,家里的饭还在锅里......"
阿纳斯后来跟我说,那天他没完成报道。不是不想,是根本举不起镜头——他蹲在废墟上,看着妻子被抬上救护车,看着女儿攥着的蓝色蜡笔断成两截,突然想起早上出门时,女儿拽着他的衣角说:"爸爸,今天能陪我画彩虹吗?"
比失去家更让他难受的,是"连真相都传不出去"的无力。加沙的网像被掐断的风筝线,电力每天只供两小时,他拍好的画面要抱着设备跑三公里去蹭联合国机构的信号,有时候传着传着就断了,再试的时候,电池已经冻得开不了机。"我不是怕危险,"他在电话里声音哑得像砂纸,"我怕那些没发出去的画面,会变成加沙的'沉默'——世界看不到,就像没发生过。"
这两天我翻阿纳斯的社交账号,最新一条是凌晨一点发的:"我把女儿的蜡笔装在采访本里了。今天拍了个老爷爷,他说'我的孙子在学校被炸死时,手里还攥着作业本'。我对着镜头说'这是加沙的日常',但说完才发现,自己的眼泪滴在采访本上,把蜡笔印晕成了小太阳。"
有网友在底下留言:"原来记者的痛,是要把自己的伤口掰开,再给世界看。"也有人说:"我们不是要同情,是要知道——每一片废墟背后,都是某个人的家、某个人的童年、某个人没说出口的'我想活着'。"还有个重庆的阿姨私信我:"能不能帮我转句话给阿纳斯?我家孩子跟他女儿一样大,我给买了新蜡笔,等和平了寄过去。"
阿纳斯现在还是每天出去报道,只是镜头里多了个小细节——他会把女儿的照片贴在话筒上。"不是为了博关注,"他说,"我想让每一个看报道的人知道,加沙不是'冲突现场'这四个字,是我女儿的彩虹、我妻子的饭香、是每个普通人想好好活着的心愿。"
昨天他发了条语音,背景音里有轻微的爆炸声:"刚传出去一段视频,是个小女孩在废墟上种向日葵。你们看,加沙的土里,还能发芽。"
我盯着那条语音,突然想起自己当电视台编导时,跟着记者去灾区采访的场景——我们总说"客观记录",但真正的记录,从来不是隔着镜头的"旁观",是把别人的痛,放进自己的心里。就像阿纳斯说的:"我不是英雄,我只是个想把家里的事,告诉世界的爸爸。"
而我们要做的,就是接住这份"告诉"——哪怕只是多转一条朋友圈,多留一句"我看见了",也是给加沙的春天,多攒一粒种子。